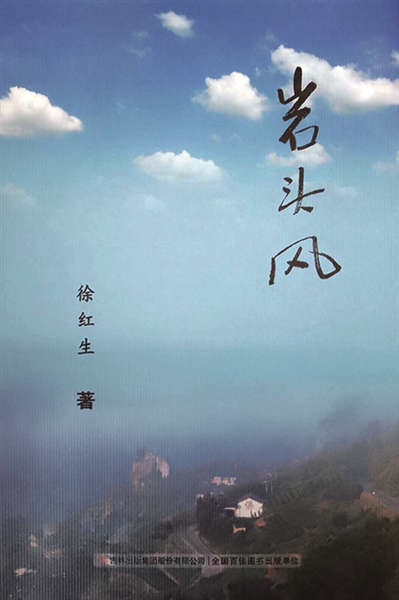徐红生老师继散文集《岩头草》出版后,今又结集出版了微型小说集《岩头风》,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!
徐老师是一个有才气、有情怀、会写作、真正称得上有“文人气质”的语文老师。他写的散文,写的是熟悉的生活,抒的是别样的情怀。他写的小说,尺牍之间,纵横千里,发挥了他擅长接地气与魔幻相结合的笔力。
在《岩头风》集子中,他讲了好多故事,他讲S市、S中学的故事,故他的微型小说可读可赏,可闻可辨。好多作品,如《黑板白皑皑》《敲门》等,与其说是小说,倒不如说是故事。小说注重细节,故事讲究情节,细节是缓慢的甚至是心理一闪而过的“镜头”,而故事情节,是动态的,是一种事件发展的必然过程。徐老师的小说,严格来说并非真正的小说,因过多考虑了情节设置,虽然这些情节并不怎么曲折生动,但细细体会,在脑中还是常常会留下该故事本身的深刻印象。
如小说《敲门》,写的是余老师的故事。从一次体检报告引出,身体素质变好,接着回忆了余老师还是小余老师时候的生活,重点讲了敲错门的故事。我们通过作品的阅读,明白了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的道理。徐老师的微型小说,小说和故事傻傻地分不清,从另一个角度说,是小说还是散文同样也难于界定,可以这么说,是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“互文”文体双生花。读《岩头风》的好多作品,会觉得它们不很像小说,却更像散文,最典型的就是《王永》一文。
小说一开头写道“熟悉的人就呵呵地笑了,老师这么写,真的还是小说?小说,不是要用虚构吗?……”在第二段中,徐老师继续这样写道“先前我写散文时,有的就当小说写,大家认为是真的。如今我写起微型小说来,熟知常识的人都知道:姓名可假,地名可假,故事也可假。假作真时真也假了,谁叫我自我标榜现在写的是微型小说呢?至于是否真假,只得请各位熟悉的人自我评判,不熟悉的人当小说读肯定不会错,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”,玄玄乎乎,真真假假,这样一番调侃,给他的作品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这个作品有散文之嫌,是因为采用第一人称叙述,叙述又很逼真,特别是有很多真实的细节,如“2016年,我出了一本散文集”,这是一个事实;作品还偏于创作主体体验性表达,具有情感表达的内在性和直接性,“王永,是我三十多年教书生涯中最有文德礼数的学生。每年教师节、春节都会收到他的短信,不论在天涯还是海角……”“知礼用礼,礼行天下。我的学生王永,虽读书不多,却懂得大道至简之理,并付诸行动。”
在徐老师的小说作品中,非虚构写作的特点是很明显的,基于真实题材,但作了一定程度的虚构,如《岩头风》《老汪退群》《不要纠结了,来吧》等。与虚构写作相比,“非虚构写作”的优势在于其与现实的关联。徐老师的微型小说集,虽然篇幅短小,但是挖掘深刻。这正如徐老师在作品《我以为是小说》中写道的:“我发现余老师的微型小说,扎根于生活的沃土,绽放出思想的花朵。”以“我”的视角谈了对余老师作品的看法,其实是徐老师巧妙地评论了自己的作品集《岩头风》,表示了对自己作品的认可,这句话对《岩头风》思想内容的评价,笔者认为是恰如其分的。
生活是创作丰富的源泉。马尔克斯谈写作时曾说过“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”的话,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,是对世界的揣度。徐老师爱生活,爱脚下这片土地,他秉承这一创作宗旨,将溢满深情的文字植于这片热土。如《手机》《敲门》《外公》《三株早笋》等,很有生活的影子。更重要的是,因徐老师的教师身份,故作品更多地写及教书职业和校园生活。S中学是一个文学概念,是小说中许多人物成长与活动的地域,小说《新来的孔校长》《我以为是小说》《位小乾坤大》《衬衫》等,都有涉及。写自己熟悉的生活,是《岩头风》最大的亮点,只有写熟悉的生活,让一切在自己的掌控之内,这样的小说品质才真诚可信,从而打动读者赢得青睐。
徐老师的小说有大境界。如作品《画家》,塑造了一个钟画家的形象。对于钟画家的成长,三言两语点化了钟画家的进步,“有我无他”“有他无我”“我中有他,他中有我”,再来一句“画家就名副其实了”,轻轻松松的一句,但可以想见钟画家成为画家的不易。
下面的文字中提到了画家的卖画作,人们对于钟画家的画作好卖却卖得少的不解,钟画家的回答“画家要有忠实、诚恳的性格……要经常考虑自己的画,要实在,要深厚,要有永久的性格”“人之立世,贵在立‘品’”,钟画家有着精湛的画技,更有诚实敬业、坚守理想的品质,以诚实的品格守护着良知,我们就始终存有希望了。
笔者评析了《岩头风》的文体特点后,再来谈点小说的创作手法。《岩头风》作品集的创作手法是多种多样的,可以说是多种手法的结合体。小说采用独特的叙事视角,突出了人物的心理;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,使文章具有了“神奇现实”;设置悬念、铺垫、伏笔等手法,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
悬念、铺垫、伏笔创作手法运用得非常好。如《你认不出我是谁了吧》《大鱼“游”上桌》等,题目就是一个悬念,很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。又如《陪衬》“余妻的好坏说,关键是与谁站在一起”,自此揭开谜底。
悬念是小说中某一个让你牵挂的“点”,它激活了读者的“紧张与期待的心情”;铺垫是提前做的基础性描写,为后面的主要情节蓄势;伏笔则是前段为后段所作的提示或暗示,它促使结构更严谨、情节发展更合理、前因后果更分明。
最后要提及作品的语言,语言质朴无华,多用口语,很亲切,很耐读,如《陪衬》“丈母娘穿了一件驼红色的外衣,好像一株红了的水杉”。
徐红生老师深谙微型小说创作的内在奧秘,拥有特异的审美取向与独到的艺术特色,那就是怀揣人文写现实,在敏感而细致的人性触摸中,时见一颗忧思深远的心。在笔者看来,以讲故事的方式,以“非虚构”的叙述,以篇幅的短小,却又以负载的深厚,让人读来深受启发,这正是徐老师小说的内功与魅力所在,也是徐老师文学写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。
□黄宝镄